□ 张儒学
在我的记忆中,院子前有很多竹子,所以我从小就爱竹。
我的老家在一个小山坡上,房前屋后都是竹子,那些竹子不是毛竹,更不是斑竹和水竹。而是一些能编竹席的慈竹。
虽然我不知道这些竹子是哪辈人栽的,但整个院子都掩映在竹林丛中,不论严寒酷暑,竹子都是青青的、茂盛的,小院里似乎就有一种仙境般的幽雅与别致。天热时,竹林里是乡邻们乘凉避暑的好去处,冬天,别的树木落叶枯黄,但院前的竹子依然挺拔且充满生机,将小院点缀得格外美丽。
在20世纪80年代,竹子似乎成了我家的“摇钱树”,会编竹席的母亲就靠这些竹子,支撑着家里的零用开支,养活了我们一家人。
在村里,编竹席的人家全是买竹子,我家则是自家栽的,不知让多少人羡慕,都说我家有眼光,栽了这么多竹子。父亲只要一有空就砍竹子,饭前饭后忙着弄篾条或帮母亲编竹席。编竹席虽然辛苦,但一家人却其乐融融。
那时,竹子在我心目中就像父亲一样坚强、朴实,不管多大的风霜雨雪也压不倒它。也像母亲一样勤劳、善良,总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小院和家人。一年四季,父母都靠编竹席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,一张张凝聚着心血、充满着希望的竹席,不知给父母带来多大的欢乐与欣喜。
因此,竹子就成为我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也因为我家房前屋后的一大片竹子,常有小伙伴儿来玩耍,在竹林里捉迷藏、打闹、玩“猪八戒背媳妇”等游戏,童年那快乐的笑声常常在竹林里回荡。
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,我常常端几盆水,用手泼给竹林,我喜欢看它洗礼后的清纯和那留在片片叶子上的“小太阳”。
下雨天,我站在竹林旁和竹林一起淋雨,去感受只有在雨中才有的快乐和顽皮。炎热的夏天,竹林遮严了宽敞的窗户,屋里便凉丝丝、清幽幽、香喷喷。月夜里,躺在床上的我,总爱沿着窗户看去,竹子闪烁着深绿、嫩绿和银白色,细碎、零乱而稠密,好似一幅流淌的玻璃画,让我那充满青春的梦想变得格外绚丽。
我在城里上学时,常想着老家的竹子,虽然城市里没有竹子,但却从书上读到了郑板桥的《竹》:“一节复一节,千枝攒万叶。我自不开花,免撩蜂与蝶。”
从此,似乎对竹有了更多了解。竹不开花,它没有牡丹的高贵,没有君子兰的艳丽,也没有月季的引蝶浓香,更没有茉莉的诱人清香,但它朴素,不炫耀,不卖弄,坚定自己的信念,真实地生活。竹刚直挺拔,也柔软曲折,刚柔相济,曲直一体,展现出它独特的美。
后来我家从小山坡上搬至相距不远的公路边,我们兄弟几人都长大了,在外面工作,很少回老家。当时,父母说什么也不愿搬出来住,他们说舍不得老屋,更舍不得相伴相依的竹子。虽然家里再也不靠母亲编竹席来维持生计了,但父亲仍旧视竹子为“宝贝”。没事时总要去挖泥巴垒竹子,正是父亲的精心管护,每年开春地上总会冒出许多尖尖角儿——竹笋,毛茸茸的黄里透着绿,不几日就长了十几尺高,父亲看了甚是欢喜。
随后,一根一根的竹子挤挤挨挨,给小院增添了几分生气。母亲依然用竹子来编竹席,这已经成为她的习惯,似乎编竹席就是母亲最好的休闲方式了。
几年前,老屋因年久失修垮塌了,父母说什么也不愿来城里住,就住在公路边的砖瓦房里,仍与那老屋前的竹子相守相望。当他们看见老屋前的竹子突飞猛长,一根一根的竹子茂密旺盛直指云天,勾勒出一幅幅立体几何图时,总是高兴不已。父亲没事时就去竹林里走走,有时还与竹子说话。母亲没事时也去那竹林里看看,对着竹子唠叨,这时的竹子就像一个听话的孩子,在轻风中摇曳,一会儿直立,一会儿弯曲。
每次回到老家,父亲都要领着我去老屋前看看,虽然老屋已变成了一块菜地,再也找不到老屋的踪影,但房前屋后的那些竹子,却勾画出老屋的轮廓。我问父亲:“四周都是竹子,你这菜地里的菜还怎么长呀?”父亲说:“我把这儿弄成了菜地,并不是为了种菜,只是为了更好地管护竹子,让它们做个伴。”
一阵微风吹来,竹子随风摇摆,竹林里响起“吱吱”声,似乎还在讲述着老屋里的甜蜜往事,还在回味着老屋里的欢乐与温馨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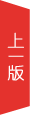



 前一期
前一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