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郑志文
又到清明。沿街的烟柳在风中摇曳着嫩黄的身姿。潞州区花园街口东北角的那株玉兰似乎很懂我的心思,在一场淋漓的夹着雪花的春雨中,孤独地、早早地、白花花地盛开了——多像母亲温暖而慈祥的白发啊。
老院子不见了,母亲已离开我38年。中午,妻子做的含有土豆、豆角、南瓜的和子饭,不经意间再一次刺激了我的味蕾。我再一次想起母亲来,想起母亲做的和子饭。
小时候,家里穷,喝一顿和子饭也是一种奢望。每当母亲告诉我,晚上要做和子饭时,我总是一个下午紧紧贴在母亲的影子里。看她从老堂屋门外的墙上摘下上年秋天攒下的已经风干的没筋豆角,挖几颗发芽的又丑又小的土豆。等那口崴脚的五升米锅水开了,母亲会先挖一勺带皮的圪糁倒进去,舀走浮在上面的圪糁皮,然后把土豆、豆角放进去,再把大颗的盐豆放一把。天慢慢黑了,锅里的一切也熬好了。这时候,母亲总会给我盛一碗圪糁汤,然后再用一把勺子从瓦罐中挖点仅剩的豆面。母亲和的豆面很硬,擀的时候也很吃力。我就站在她的身旁,等擀好切面时,我会拽一拽母亲那虽然破旧却很干净的蓝围裙。母亲当然知道我想干什么,她会切下一小片,笑盈盈地看着我,把它放在火口上烤一下,等面皮起泡了,母亲会把它翻过来再烤一下。等母亲说可以了,我会一下子抓起来,像抢什么宝贝一样,顾不上烫嘴不烫嘴,一边“狼吞虎咽”地吃,一边仰头望着头发花白的母亲。
那时候和子饭不用佐料,最多也就是用铁勺烧一下,抹一点油花。尽管如此,那样的味道早已融入我的生命。每想到和子饭,我总会有种莫名的情感在潜滋暗长。
等饭好了,母亲会在黑暗中抱着我盘坐在用玉茭皮做成的垫子上,等父亲兄长和姐姐回来。尽管我很饿,但家中的规矩是不允许上地的大人回来之前吃饭的。
又是一年清明时,和子饭成了我与遥远的母亲交流的方式。现在的我,也会做和子饭,虽然没有母亲做得那样纯、那样香、那样美,但总能在慢慢做、慢慢品、慢慢咽的过程中积淀厚厚感恩、沉沉思念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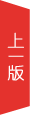



 前一期
前一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