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冷桐
每到冬至,奶奶都会给我打电话:“快来吃饺子。”
北方人有两个重要日子必定吃饺子,一个是团圆的除夕夜,男人们扶着桌子行酒令,女人们围着灶台下饺子,烟雾与蒸气一同氤氲在屋子里。另一个是冬至,据说是为了防止冻掉耳朵。由此可见,饺子在北方人心中,是一种无可替代的美食。
我从小吃的饺子馅儿多是胡萝卜搭配羊肉。冬天的清晨,窗户上会结一层冰花,儿时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屋子里会结冰,嚷着“玻璃漏水”,惹大家笑话。这个时候奶奶就已经系好围裙,坐在桌前揉面。爷爷则拿出一个搪瓷盆,将搅碎的羊肉和胡萝卜拌匀,抹上一层薄油,再加上十三香、料酒、酱油等调料,然后用筷子尖挑出零星一点碎末,放在嘴中尝尝咸淡。
饺子皮以看不清的速度变薄变大,放入一勺馅料,再一折、一收、一紧、一攥,一个大肚“元宝”出现在掌心。奶奶包的饺子并不大,小巧玲珑卧在盘中。年幼的我负责将它们放在竹篦子上,排列成好看的队形。这项富有诗意的神圣任务,让我感受到饺子的美。窗户上的冰花逐渐消融,奶奶擀面的速度也逐渐变缓,太阳隔着水珠浸染的玻璃,将日光披在奶奶的围裙上。
除了摆放饺子,我还主动承接煮饺子的活儿。饺子在我的指挥下,一个个前赴后继、义无反顾地跃向滚烫的锅里。我用笊篱贴着锅底,轻轻地推动,让沉在下面的饺子,继续翻滚。点过水后,那圆滚滚的饺子慢慢涨着肚皮浮在水面,一笊篱下去,像网起一兜锦鲤,在盘子中打挺,胡萝卜的颜色透过面皮若隐若现。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,再往碟子里倒入必不可少的陈醋,醋香裹着面香与舌尖碰撞,牙齿在酸味中感受馅料的鲜味,蒸气将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。
当我踏进家门,奶奶坐在桌前揉面,爷爷端着不锈钢盆从厨房走出来,问我要不要尝一尝馅儿的咸淡。我问是什么馅儿,爷爷笑着说:“胡萝卜羊肉馅儿,你想吃素饺子吗?”
我说都行,反正吃不了多少。奶奶这才拍着脑门说:“我都忘了,你小时候能吃四十个饺子哩,这又包多了。”
现在我恐怕只能吃二十个饺子,但冬至这天我一定吃四十个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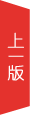



 前一期
前一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