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孙福攀
立冬的到来,似乎是被夜半一场无声的霜宣告的。
清晨推窗,一股寒意扑面而来。窗沿玻璃上凝着薄冰似的霜花,随意勾连却清奇错落。目光向下,几片从银杏枝头脱落的叶子,昨日还铺展着温暖的明黄,此刻却已经僵卧在石阶,被彻骨的银白严严实实地包裹浸染了。那霜痕像是活了,沿着叶脉纤细的骨架、蜷曲的边缘无声流泻、悄然漫涨,将它凝固成一片通透而脆弱的玉石雕件,寒意从这小小的冰壳里幽幽渗出来。枯草顶着绒白霜冠,细枝横斜,亦如银装素裹的微型森林。四下寂然无声,连平日里最聒噪的麻雀也噤了声,只在远处电线上瑟缩成一小团毛球,世界仿佛被这初生的冬霜施了定身魔法,成了一幅清冷到极致、洁净到极致的晨景。
霜气侵肌,寒意砭骨,不由得缩回窗内。厨房里炉火已生,灶上的小铜壶正“滋滋”吐着热气,白雾弥漫着湿润暖意,将冰冷的空气撕开一道柔软口子。掰下一角珍藏的陈年普洱,投入一只厚实的白瓷小杯,滚水冲注的瞬间,深沉的赭色茶汤迅速漾开,如墨入水,丝丝缕缕的金色茶毫在杯心旋舞,醇厚温润的茶香袅袅升起。小心捧起这半盏温茶,手指最先感到那份实在的暖意,缓缓贴近唇边,微啜一口,茶的热流带着木质特有的甘香滑入喉中,馥郁绵长,所过之处,那股被寒气裹挟的瑟缩,便如坚冰遇着阳春,悄然瓦解、消融。那温烫像一条苏醒的小溪,从容而有力地流淌至四肢百骸,驱散最后一点滞留在关节深处的僵冷。寒意被茶水驱退大半,这才发觉自己的肩膀不知何时已微微佝偻,此刻也舒展了。唐代的白乐天道“霜轻未杀萋萋草”,这新霜固然未冻杀萎草,却实实在在地催索人寻求一份贴近骨肉的慰藉。添衣抱炉暖身,饮茶暖腹暖心,是时序轮转里最本分也最熨帖的回应。
茶汤温了两三巡,屋里的暖意和茶香愈发浓郁。家人也围坐桌前,各捧一瓷杯。父亲煮茶的功夫深,耐心守候,每一道水的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。茶味渐渐柔醇,话题也随之漫开,水汽氤氲里从窗外的霜景聊到冬日腌菜的琐碎,无甚大道理,也无急切之事,句句不离烟火家常。炉火映在杯壁的水纹上,荡漾着细碎微光;浅褐色的茶垢嵌在杯沿,沉淀着年深日久的温存。时光被室内的暖意和这绵密的声音所浸润,变得悠长而滞缓。古人说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”,那份邀友围炉、消磨寒夜的意趣,此刻在寻常家人闲坐,茶香氤氲的日常里,竟也体会得七八分。所谓节气深情,非必宏大叙事,常落于此等氤氲热气、絮絮笑语交织的画面里——室外的严霜是天地画的工笔,这半盏茶、一盏灯,絮絮数语,便是人间回赠的写意温暖了。
霜气是冬的笔锋,在大地上刻下的寒章,冷冽、晶莹而寂静。
而那半盏温茶腾起的热,则是人心在书页间落下的注释,微小、柔和,却足以穿透纸背的冰冷。当霜华在窗棂细密铺陈之时,恰是小炉烹茶、闲话初沸之刻。这冷暖相映之间,季节流转的深意,便如茶汤回甘,从舌尖悄然滑落心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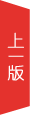



 前一期
前一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