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汪翔
北风如矜持的笔触扫过大地,天地骤然疏朗清明。远处的山被一层淡淡的雾霭笼罩,若隐若现。枯黄与褐红攀上山峦,宛如一幅淡雅的素描。
进入12月,小草褪去了夏日的青翠,尚余一抹淡淡的绿意,如同生命的脉动,在寒冷的季节里,展现着生命的顽强与美丽。土层之下的草根沉默蜷伏,攥紧绿色的初梦。杨树的叶子落得干净,枝丫朝向天空。几畦青菜,叶片上凝了一层薄霜,白中透着青。纵目四望,草地、田畴、菜畦、杨树,分散搭配恰到好处。在田野中行走,脚下松软的泥土传来阵阵清香,久久不散,又在酝酿新一轮的生长。
家乡的河水脉络清浅,在阳光下闪烁着银光。河道弯曲,河水清澈,倒映着天空中的云彩和远处的山峦。
风是一把无形刻刀,将水面雕琢出细密纹理,一群野鸭悠然自得地游着,时而潜入水中觅食,时而浮出水面嬉戏,为宁静的河水增添了几分灵动。雪白的芦穗像一支支饱蘸诗情的毛笔,在风中摇曳,发出簌簌轻响,仿佛是冬日的舞者,诉说着古老的传说。
落叶翻飞,飘逸如云,飞舞中透着灵气,用手触摸,软绵、蓬松,十分轻盈。河边的柳叶、枫叶早已飘落,细长的叶,五角的叶,伴着缤纷的色彩,河面荡起一圈圈细腻的涟漪。那条长长的小河,转瞬变成了一幅美丽的长卷,阳光投射过来,画卷上透出金色的光芒。那是冬的杰作,是风的手笔。
冬日的山峦,秋的浓郁还未离去,清寂已然到来。山峦层叠处,绿、红、黄三种色调互相交织,又层次分明。大多数树木褪去了繁密的枝叶,露出瘦硬遒劲的筋骨。枝干嶙峋虬曲,枝桠疏疏朗朗,横斜交错。
那些依然顽强生长的树木,挂满了形态各异的野果,它们在寒风中傲然挺立,仿佛向世人展示着生命的顽强和不屈。枝头偶有挂着的小果子,在纯净的蓝天映衬下,犹显灵动与俊俏。在删繁就简的静美里,有一种清寂的诗意。
枝头伶仃的枯叶簌簌摇动,似悬而未决的琴音,在空中轻轻摇曳。那些深秋璀璨的红与黄零落殆尽,偶尔有几片枯黄的叶子,如同一只只疲倦的蝴蝶,在空中无力地飞舞着,最终缓缓地飘落林中。
阳光透过稀疏的枝桠,洒下斑驳的光影,如同一位油画家在缓慢涂抹。忽有雀鸟惊起,鸣声穿空,复又没入苍茫,唯余清音萦绕。山路覆满黄叶,一片叠着一片,厚厚地、松软地积着,脚踏上去,听不见脚步声,只觉一种蓬松的、酥脆的触感。
田边有两排银杏,比当年高大了许多。初冬的银杏依然满树金黄,远望过去,像是一条金色的河流流淌在谷地。扇形的叶子明亮通透,仿佛储存了阳光,风一吹,叶子便打着旋儿从枝头落下,地上就铺了一条金色的地毯,铺就一条通往童话世界的路,踩上去发出清脆又柔软的声响,那是一整个季节更迭的脚步声,是时间流转的声音。
初冬的银杏,比起春日里烂漫的野樱、夏日里繁盛的荷塘,更为动人。它的美,不在于喧闹,而在于静寂;不在于生长,而在于沉淀。它像一位阅尽悲欢的智者,将一生的故事都凝在这满树的金黄里——不言不语,却已说尽了一切。繁华到了极致,便是这般近乎肃穆的静。它并不与这萧瑟的时节抗争,只是安然地、自在地完成自己最后的绚烂。
天色渐渐向晚,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,那最后的余晖,斜斜地穿过枝桠,给这满树的黄又镀上了一层淡淡的、温润的赤金。
光与影在枝叶间微妙地颤动,整棵树便像一束安静燃烧的火焰。四下里愈发静了,甚至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,与那落叶归根时最微弱的叹息混在一处。
暮色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。屋里一家人围着一个热气腾腾的火锅,清汤锅底、几片生姜、几段大葱,汤水“咕嘟咕嘟”地翻滚,氤氲的热气把人的脸颊熏得红扑扑的。将炖好的鱼头放进火锅,添加丸子、萝卜、大白菜和菠菜,在滚汤里涮熟,蘸上调好的芝麻酱,入口是无与伦比的鲜嫩。蜂窝一样的冻豆腐,吸饱了汤汁,咬一口,那鲜美的汤就在唇齿间迸溅开来。
家乡的冬日是一幅动人的画,清寂安然,静美而从容,是一首无韵的清词,泛着淡淡的冷香,清冽而素净。它用独特的语言诉说着生命的美好与坚韧。
冬天的美,不在于繁华喧嚣,而在于那份宁静与纯粹,那份亲情,让人心灵得以沉静,思绪得以飞扬。行走在这样的冬日里,如同漫步画中,宁静且美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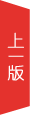



 前一期
前一期